目击一场美国版“布尔战争”

2024年5月3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萨那举行的一个集会上讲话
文/鲜甄 高玖
编辑/吴美娜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延宕超过600天,加沙北部、中部、南部轮番遭到战火蹂躏,5.4万多人被夺去生命。与冲突密切相关的另一边,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连番碰撞,也持续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等袭击红海等水域的以色列及其盟友目标,要求以方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2024年1月12日以来,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造成人员伤亡。美国今年3月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美国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发动打击。
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同意停止威胁中东水域航行安全,在此基础上美国将停止对胡塞武装的轰炸。另据胡塞武装声明,与美方达成“初步谅解”不会影响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从更广阔视野看,胡塞武装与美国的对抗,已超越地区性安全事件范畴,逐渐演变为一场体现全球战略格局变迁的“边缘战争”。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番较量俨然是一场美国版的“布尔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非对称”冲突中,胡塞武装依靠其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与“以陆制海”的地理优势,对美国高价值航母及其护航战舰形成实质性威胁。尽管美军装备精良,但在短期内却难以压制胡塞武装的频繁袭扰。
20世纪初的布尔战争是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殖民地的征服,实则暴露了帝国扩张的深层矛盾:高昂的战争成本、国内舆论的反战压力、国际形象受损以及非对称战术的消耗。布尔战争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映照出当前胡塞武装与美军冲突呈现的“美版布尔战争”的特征——全球霸权力量在边缘地带遭遇持久而低烈度、非对称却极具消耗性的战争模式。可以说,陆海军事技术的扩散与局部战争形态的演变,正在侵蚀美国所代表的海洋霸权的基础。
“边缘战争”的一种典型
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当时的英帝国在非洲大陆与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之间爆发的殖民战争。其根源在于英国企图将其在南非的殖民地与布尔人建立的两个独立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统一起来,以控制当地丰富的黄金和钻石资源。布尔人为防止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英国虽为当时全球海陆最强的帝国之一,但在面对数量与资源都远不如己的布尔游击队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尽管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却付出伤亡逾万人、耗资数亿英镑的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不仅从经济上拖垮了英国财政,也引发国际上对帝国正当性的广泛质疑。表面上这是一场“殖民与反抗”的常规冲突,其深层却反映出帝国边缘地带对中心秩序的结构性挑战。
战争初期,布尔人利用高度机动化的骑兵游击战、隐蔽地形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成功对抗英军。这种战法使英国不得不使用焦土政策(一种肆意毁灭作战区和占领区人类文明的野蛮政策)、建设集中营等极端手段予以应对,这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国际舆论反弹。战后,英国不仅放缓了海外扩张步伐,还被迫在政治上逐步接受自治领的防务自主权,从而进入“非正式帝国”阶段。
换言之,布尔战争作为一场技术先进帝国与地方游击力量的消耗战,成为英国全球霸权衰退的前奏。在历史学界看来,布尔战争是“边缘战争”的一种典型,即强权国家在非核心区域遭遇低烈度却高消耗的非对称挑战。这种模式已然构成胡塞武装与美国冲突的历史镜像。
非对称作战的当代表达
胡塞武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一个深嵌于也门北部山区、拥有宗教-部族根基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自2015年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爆发全面战争以来,其军事能力获得迅速发展。时至今日,胡塞武装已构建出一套具备近海打击能力的“混合战斗”体系,结合远程导弹、无人机、水面无人艇等武器装备,能够在红海这一国际重要航道展开军事行动。
2024年末至2025年初,胡塞武装多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红海南部海域的美军舰艇,迫使美军舰队“高价”防御。2025年4月,为躲避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美军一架F/A-18战斗机在航母紧急机动规避后坠海,造成上千万美元损失。在胡塞武装的数次袭击中,其使用的无人机和导弹造价不过数千至数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拦截一枚导弹所使用的“标准-6”型舰载防空导弹,其单枚成本往往高达数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虽然美军多次发动空袭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由于后者的分散部署与密集的地下工事掩护,其导弹发射平台与指挥网络难以被根除,美军花费高昂,空袭效果却往往大打折扣。
双方成本与战术的不对称性,构成了现代“以廉制贵”战争模式的典型样貌。在这场冲突中,胡塞武装的优势并不在于力量本身,而在于其战术灵活性、空间机动性与技术便捷性。特别是导弹与无人机技术的应用,进一步降低了胡塞武装发动远程打击的门槛。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耗费低廉的武器技术扩散,正使得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具备威胁大国高价值目标的能力。
尽管胡塞武装成功打击美国航母的难度极高,且尚未有确凿证据表明胡塞武装成功命中或重创过美军主力舰艇,但其屡次宣称尝试攻击航母舰队,本身构成了一种战略信号:通过挑战美国海军的核心象征,不断试探美国海权防御的边界,这种心理战和宣传战的效果不容忽视。
与此相对应,美军的战略反应则呈现三重掣肘:首先是战术上的高成本与打击目标的难定位;其次是战略上的选择困境,即陷入整体战略收缩与扩大军事干预的两难境地;最后是政治与国际法的合法性约束。此类困境与当年英国在布尔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僵局如出一辙——不能放任边缘抵抗组织扩张,同时又难以采取全面征服式的打击行动。
“以小博大”映射美国困境
胡塞武装的进攻能力与其对手的防御措施之间存在的巨大成本差异,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国海军霸权的战略决策。由于实力较弱的一方无需具备与其对手相当的军事实力,就能对强大的海军造成相当的损耗和干扰,这引发人们对当前海军防御战略在面对此类非对称威胁时,长期可负担性和有效性的质疑。
此外,曼德海峡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增强了胡塞武装的非对称作战能力。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约三分之二的红海沿岸地区,包括重要的港口城市荷台达和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红海最宽处约355千米,最窄处仅29千米,极大限制了美国大型舰队的机动能力和回旋空间。胡塞武装能够依托沿岸有利地形部署反舰导弹、无人机和水雷等低成本武器,对美军航母编队形成近距离威胁。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胡塞武装与美军的冲突揭示出全球海上霸权体系的某种松动。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依赖航母打击群保持对潜在对手的威慑和维持全球霸权秩序,但当前这种“海上霸权模式”正受到挑战。胡塞武装通过陆基导弹对红海海运造成严重威胁,甚至迫使多国军舰和商船集体绕行非洲好望角。有评论指出,这是西方世界自二战以来首次在常规海域放弃对关键航道的控制权。
航空母舰长期被视为美国海洋霸权的象征,而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正逐步降低这种威慑效能。在红海曼德海峡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以小博大”威胁大国海权的局面,表明未来在受争夺的海域将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此类“低烈度、多域骚扰”的局部冲突。此外,海权与陆权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胡塞武装没有蓝水海军,却能通过部署内陆武器打击海上目标的方式获得“游击式海权”。在未来战争中,航母的近海巡弋必须面对来自山地、城市甚至民用平台的威胁。陆地已不再是海洋秩序的背景,而是制海权的新前线。胡塞武装与美国海军的海峡博弈,不仅是双方军事对抗下对航道控制权的争夺,也是武装力量与地区秩序对应关系的重建。
边缘冲突与霸权衰退的历史回响
“美国版布尔战争”不仅是一种类比,更是一种判断。当霸权国家不得不反复调动大量资源应对其传统影响范围边缘地带的低烈度战争时,这往往标志着其全球秩序维持能力的边际效益递减。
英帝国在布尔战争之后,其战略核心由扩张转向维持。与胡塞武装爆发冲突的美国,如今在中东、欧洲、亚太等多线面临压力,其全球“存在能力”正在经受资源限度与战略焦虑的双重考验。正像布尔人在帝国边缘开辟了反抗殖民的战场,胡塞武装所展现的现代非对称能力也为未来类似冲突提供了“作战模板”。这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美国面临的战略与制度性霸权的挑战。
综合来看,当前形势下美国的海权优势正因武器技术进步和非国家行为体威胁而面对不同以往的挑战。这种趋势与20世纪初英国在布尔战争中所遭遇的局面有相似之处:当曾经的海上霸主在外围战场耗费巨大却难以扭转局势时,其全球实力的结构性弱点就将逐渐显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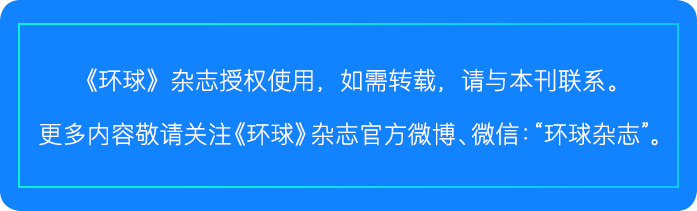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