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界遭遇“寒潮”

2月27日,一名工作人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卫生中心准备麻疹疫苗
文/《环球》杂志记者彭茜
编辑/乐艳娜
8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发表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确立了发展科学技术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政府资助-学术自由”的模式,使得二战后美国科研实力迅速崛起,美国在计算机技术、航空航天等众多关键技术领域稳居全球领先地位。
80年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仅数月,就撕毁这一“科学契约”,掀起了一场“反科学风暴”:拆解联邦科研机构、强力打压顶尖高校、大幅削减科研经费……有专家认为,凡此种种不仅给全球科学界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也会削弱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并重塑全球科研创新版图。
科学界寒潮“加剧”
哈佛大学官网上,黑底白字“研究岌岌可危”的字样尤为醒目。这是对特朗普政府无声而有力的控诉。
近期,特朗普对这所美国顶尖大学屡下“狠手”,继宣布冻结对其数十亿美元的拨款、威胁剥夺其拥有的免税地位后,又禁止该校招收国际学生。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特朗普政府居然在主动摧毁全国最优秀的研究机构之一,”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家德勒冈娜·罗古利亚说,她所在实验室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已被终止,结核病、渐冻症、癌症演化等多项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研究因此停滞。
美国政府与研究型大学之间几十年来的亲密合作关系已岌岌可危。以“反犹主义”指控为棍棒,特朗普政府已威胁要调查数十所大学,并停止向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拨款。这一系列行动还包括取消研究经费、要求撤销多样性行动、调查和逮捕部分外国学生和学者等等。
除上述顶尖高校外,一些联邦科研机构更是被特朗普政府粗暴“拆解”。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文件及来自研究人员的资料显示,今年2月至3月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约780项经费被全部或部分终止发放,涵盖疫苗、公共健康和艾滋病等关键领域。

5月2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
据《自然》杂志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家队伍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头三个月里大幅缩减,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科学机构的数千个岗位被裁撤。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约1900名成员代表全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联合发布公开信称:“我们正在发送求救信号,敲响警钟:美国的科学事业受到了重创。”
未来,这场席卷美国科学界的“寒潮”恐将加剧。《科学》杂志报道称,特朗普2026年的预算提案意味着对科研领域的“灾难性”削减。这一预算要求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出削减37%,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出削减超50%。白宫还试图取消联邦政府对气候和生态研究的大部分资助,并将美国航天局的科学预算削减一半以上,取消主要的行星探测任务……
“当科学被‘工具化’之后,基础研究和长周期的知识积累就被边缘化,而这些恰恰是美国科研长期领先的重要基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主任周程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难以修复的裂痕
二战后,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国家科技体制的建立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帮助美国摆脱了对欧洲基础研究的依赖,奠定了其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的地位。由政府出资,联邦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同为创新发现的引擎,诞生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疗法等诸多造福世界的科学创新。美新政府一系列“反科学”举措,相当于直接斩断了联邦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驱动的“左膀右臂”。
与注重“短期变现”的企业资助相比,政府资助中相当大比例是用于支持能推进人类认知前沿,但短期内尚无法投入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2023年,美国大学研发投入达1090亿美元,近600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
基础数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往往距离现实应用相当遥远,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以“隐形”的方式,持续为更广泛的科研生态系统注入动力,最终间接促成实际应用的产生。著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日前在其个人博客上直言自己的研究经费已捉襟见肘。他认为,对基础研究的资金削减,会影响新一代科研人才的成长。长期来看,将大大削弱人们解决现实重大技术难题的能力。
美国历史上,麦卡锡时代的政治干预曾导致美国物理学十年停滞。当时的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大规模调查科学家的政治立场,大量被调查的科学家被迫离开学术界。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也因参加过左翼政治组织的活动受到政府安全审查。其结果是,联邦科研资金向军事技术严重倾斜,对基础物理学的资助比例下降。
“与麦卡锡时代相比,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对美国科研创新的冲击更系统化,影响更为巨大,且修复艰难。这种信任崩塌与制度损伤的修复需数十年,因为科研生态的恢复不仅依赖资金,更需重建国际社会对学术自由的信任,而后者一旦瓦解便极难复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汝鹏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说。
《自然》杂志开展的读者调查显示,近1600名受访者中的94%表示,他们为美国科学的未来而担忧。
全球科研合作也因此遭受重创。“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冲击国际科研合作的传统框架,受阻最严重的领域集中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层面。”汝鹏说。在气候研究领域,美国削减相关科研经费,退出部分国际气候科研合作项目,使全球气候科研合作进程受阻。在公共卫生领域,限制数据访问权限、切断与国际卫生机构联系等,影响到全球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
据《自然》杂志报道,特朗普上台后已削减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全球卫生支出。报道说,2024年美国在全球卫生方面的支出约为120亿美元,一项利用模型估算的研究显示,如果没有这笔年度支出,未来15年内全球包括美国人在内可能新增死亡人数约2500万。
出于对赴美访问的担忧或预算缩减等问题的担忧,全球科学会议也纷纷撤离美国。因担心参会人数,比较认知国际会议历史上首次将明年年会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受联邦资金削减影响,国际认知行为治疗协会取消了原定于今年8月在田纳西州举行的会议。
撕毁科学政治契约
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界的打压,反映出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政治界对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在特朗普的政策构想中,科学变成了一种其所谓直接服务于国家竞争力的技术工具。
相关专家认为,以“优化资源配置”名义大幅削减科研预算,以此缓解财政压力是特朗普系列动作的最直接动因。汝鹏指出,白宫2026财年预算大幅缩减非国防科研预算,本质是以短期经济收益优先,忽视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
其次,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立场与高校中自由派、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夺回高校话语权,将高校变为其政治发声阵地。比如将气候变化、性别研究等议题污名化为“自由派议程”,并通过审查制度排除异见,如审查高校多元包容计划等。
事件更深层面的动因,则是科学自主性与被政治工具化的冲突。二战后,《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奠定了美国“科学-政治”的契约关系,强调科研自由与公共性。历史上,美国政治界与科学界虽偶有摩擦,甚至哪怕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对科学界也多有打压,但上述契约关系仍旧得到维系。
“但此次特朗普政府试图以政治优先级替代同行评议,将科学降格为‘国家竞争工具’,对科技界和高校的冲击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将在相当程度上颠覆美国二战后科学与政治的契约关系。”汝鹏说。
周程则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框架可视作科学的再工业化与再政治化,体现了科学与产业政策的深度捆绑——人工智能、自动化等被视为可直接转化为经济与地缘优势的“效用科学”,得到优先扶持;而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短期收益不明确的基础研究或精英大学,则被置于审查与经费重塑之下。

研究人员在美国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一实验室进行月壤相关研究
全球科研版图或重塑
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和开放合作的学术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诸多受访专家认为,长期来看,特朗普政府一系列举措将削弱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全球科研版图或将由此走向多极化发展。
据多家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已暂停新的学生签证面谈,同时考虑扩大对国际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审查范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员基伦·弗拉纳根说,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创新的引擎,并培养了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人们曾认为美国科学体系具有独特的稳定性,但现在“这种稳定性已不再有保障”。
对学术圈的持续打压,已使美国科研人才外流加剧。《自然》援引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专注于科研人才职业发展的“自然职场”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3月,美国科研人员提交的海外工作申请较2024年同期增长32%,在该平台浏览海外工作岗位的美国用户数量同比增长35%。
“更重要的是,美国科研系统的‘象征意义’——即把科学视为公共利益、将知识分享作为全球责任的理念,也正面临侵蚀。”周程说,一旦科研不再被视为公共品,而被当作国家博弈的资源,那么美国作为全球科研领导者的正当性,也将逐步失去基础。
与美国“大刀阔斧”赶人相比,多国正抓紧“捡漏”,斥巨资引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月宣布总额5亿欧元的“选择欧洲”人才吸引计划,称要“让欧洲成为吸引研究人员的磁石”。欧洲研究理事会也宣布将打造人才“避风港”,为移居欧洲的研究人员提供的额外“启动资金”翻倍至最高200万欧元,用于建立实验室等。
法国启动“选择法国科研”平台,吸引国际学者赴法或赴欧开展研究;澳大利亚科学院4月宣布启动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以快速招募美国顶尖科研人才,称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汝鹏认为,美国高校吸引力下降,欧洲、亚洲多国高校可能借此机会增强自身影响力,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不再过度集中于美国,部分新兴国家科研实力有望提升,逐渐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这不仅是人才流动,更是科研结构的重新布局。”周程说。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构建本土化的科研高地,例如围绕AI、绿色能源、医学工程设立特区或国家实验室,把人才、经费和产业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类似“微型硅谷”的集群。长远来看,全球科研或许将更趋向“多中心化”,即不再围绕单一国家展开,而是多个区域力量在不同赛道上形成各自优势。
“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合作空间,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如果不能重建对科研多样性和开放性的信任基础,它在未来全球知识秩序中的话语权将被削弱。”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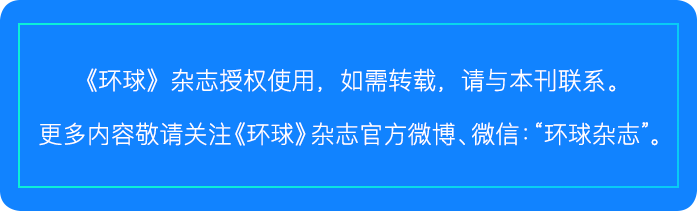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